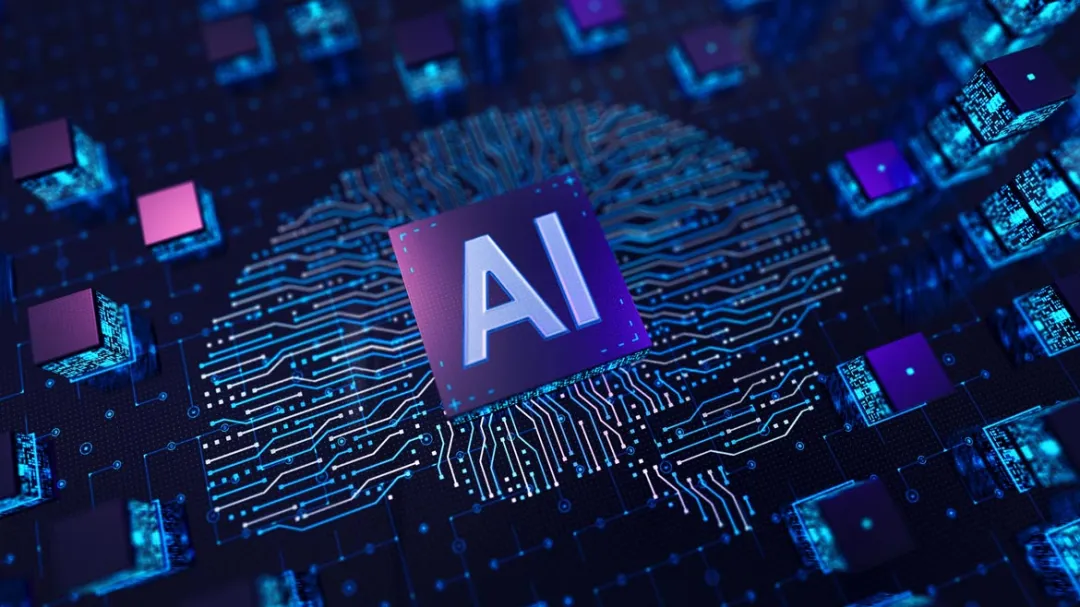
我们为什么要构建一个人类必须与机器竞争的社会?
在DeepSeek用代码绘制的新世界里,机器开始理解情感、创造艺术、决策战略。随着AI逐渐发展成熟,创造出AI的人类究竟会成为造物者还是被控者?我们与AI的关系是恐慌替代还是协同进化?探寻人机共生的底层逻辑与利弊,我们应该怎样定义AI发展的目标?
从技术层面来说,给AI编程目标并不困难,其难点在于如何让机器达成共识,当前普遍的看法认为,人类群体甚至都难以达成共识,更何况机器。实际上,在Max Tegmark看来,尽管人们会争论哪种食物更美味、社会应该如何组织等,但几乎全球所有国家都认同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,包括消除饥饿、保护环境等。其实人类在许多基础目标上早已形成默契,只是习以为常所以不再谈论,如何让AI认同这些基本目标,正是尚未解决的安全问题的核心所在。我们应当先攻克这一难题,不用太过纠结人类存在分歧的次要目标,它们只是细枝末节。
这也是Max Tegmark提出“生命3.0”概念的初衷,我们都憧憬着一个人人充满同理心与爱、紧密连结的未来,但从现状到理想世界仍困难重重。当前研发通用人工智能(AGI)的企业是否真的在帮助我们迈向“生命3.0”,仍待验证。我们既需要发展出更强大的AI,更要确保对其的控制力。
当前的困境在于,尽管各国企业领导者都向往美好未来,但激烈竞争迫使他们在安全问题上走捷径,优先追逐短期利益,忽视人类的安全福祉。毫不夸张地说,我们正在制造的只不过是能为制造者赚钱的机器。如果放任用机器取代人工的企业淘汰传统企业,AI决策的公司碾压人类管理的公司,AI指挥的军队战胜人类军队,AI管理的国家超越其他国家,届时人类将置身何处?我们创造的世界将不属于人类,这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,也不符合人类文明的根本诉求。
过去全球政界普遍将人工智能与国力直接挂钩,认为“多多益善”。但如今人们逐渐意识到:无论是哪个国家率先开发出人类智能,在尚未掌握控制技术的当下,都将可能导致人类文明终结。这种认知转变使各国利益达成空前一致:人类不应急于创造超越自身掌控的超级存在。
我们本可以借助科技创新享受更美好的明天,解决现有的问题,甚至探索宇宙的奥秘,为何要冒险葬送这一切?我们今天之所以急于求成,都是源自于竞争压力,但这与人类整体命运相比,完全不值一提。
更让Max Tegmark担忧的是,某些科技巨头发展过于迅猛,以至于能够干预政治、游说政府,在经济领域已初现端倪,为我们敲响警钟。假如人工智能领域重蹈覆辙,我们在未来可能见证雨林消失、社会礼崩乐坏、全民陷入精神困境,最终彻底丧失对文明发展方向的主导权。
Max Tegmark有三个孩子,他坦言,每当自己看着仅八个月大的儿子的眼睛时,内心总感到担忧。虽然孩子逐渐学会说话,各项能力也日益精进,但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会比他的成长速度更快。未来,面对充满疑虑、向他寻求建议的孩子,Max Tegmark唯一能确定回答的是: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巨变。
过去“寒窗苦读二十年、按部就班四十年”的范式已经过时,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灵活性,并做好需要不断适应的心理准备。然而,当前的教育体系恰恰很难传授“灵活性”,即便是在MIT教学的Max Tegmark,也承认MIT变革的速度都不够快,现有教育体系亟需变革。
在适应未来的教育里,批判性思维至关重要,可以让人具备独立判断能力,避免被轻易操控。同时,所有人,包括从未学习任何有关AI知识的非专业人士,也必须密切关注AI在自己所属领域的最新动态,思考如何将其转化为自身优势。当前趋势表明,真正的竞争鸿沟并不是人机对抗,而是善用AI者与尚未掌握AI工具者之间的差距。
若人类决定继续发展超级智能,未来5到20年内或将出现以电力成本就能全面超越人类工作效率的机器,届时社会必须建立保障体系。政府需要通过税收或其他方式,让技术持有者或相关企业承担责任,确保每个人都能享有充实且幸福的生活。此外,也要明确划分AI的工作范畴,如教学、育儿、景观设计等领域,即便AI在这些领域中可能更高效,我们仍可选择保留这些赋予人类意义的职业。归根结底,我们为什么要构建一个人类必须与机器竞争的社会?政府的根本使命是保障人民福祉,而非服务于机器的利益。


